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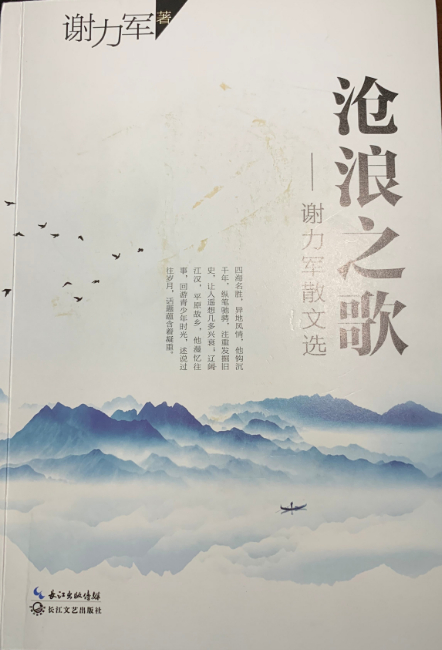
4月24日上午,《沧浪之歌——谢力军散文选》作品研讨会在武昌群光广场钟书阁举行。

参与研讨会的嘉宾留影
张艳君诵读《沧浪之歌》片断
《沧浪之歌——谢力军散文选》系长江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一部文化散文集,作者谢力军是一位有医学专业背景、长期从事医务教育工作的学者型自由写作者,多年来在传统文学刊物和网络平台发表了多种文体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诗词作品等,发表于《芳草》杂志的中篇小说《医药魔方》曾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其以“万千悲欣付沧浪”的情怀写出的这本散文集,题材广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纵笔山川名胜、古今人物,既写神农百草,也谈音乐美术;既品楹联诗词,还论训诂文字……引经据典无掉书袋之嫌疑,文笔老辣有炼字句之功力,感时伤往,悲天悯人。在人文精神日渐缺失,低俗文化恶性泛滥的当下,谢力军先生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能浸淫文史哲等领域,沉心静性坟典索丘,孜孜以求探幽寻微,且有如此成果,实属难得。

研讨会现场
作品研讨会由武汉散文学会主办,著名评论家樊星,著名作家任蒙、田天、刘爱平、钱鹏喜、黄土,著名诗人解智伟等到会,并对作品进行了精彩评析。
谢力军致答谢辞。

谢力军致辞
他对大家的点评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说,他创作的作品大多来自于养育自己的故乡--湖北天门。故乡门前有一条襄河,是汉水支流。汉水虽然没有我们母亲河黄河、长江那么伟大,也没有淮河、大运河那么辉煌,但因为有汉水,其发源地起名汉中;因为刘邦在汉中封汉王,才有他的国号“汉”;因为汉朝,我们的民族、同胞、语言文字和文化均冠名为“汉”,这里和三楚大地永远是我创作的源泉……
在作品诵读环节,朗诵家张艳君诵读了《沧浪之歌》片断以及解智伟的诗歌。声情并茂的朗诵很好地诠释了作品的内涵风格,引发了在场来宾的共鸣。最后的签名售书环节读者踊跃,场面热烈。
钱鹏喜主持了今天的作品研讨会。
谢力军代表作品链接:
襄河谣
沧浪亭下水沄沄,岳市樯竿簇夕醺。
独向沙头吊遗迹,当年曾驻岳家军。
——清.岳口诗人张其英
一
岳口之名,从晚唐时期追仰风雅的“约价口”,到南宋年间洋溢豪气的“岳家口”,再到近现代口碑相传之“小汉口”。名称演变,反映了本邑世代黎庶“敝帚自珍”的心思,也有赖五湖四海各路朋友的倾力抬爱,是千百年间众爱与自爱、表扬与自我表扬的结果。
汉江沿岸地名带“口”字的有多个,岳口上游有襄阳老河口、潜江泽口,下游有汉川马口,和天下闻名之大汉口。与上下诸“口”相比,岳口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天、潜、沔交界处的汉水之滨,独占“形胜之要”,千年风云际会,成就了一个“内河经济圈”的奇迹、“水”的奇迹。

航拍岳口之襄河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汉江作为一条没有单独入海口的长江支流,能与长江、淮河、黄河并驾齐驱,足见其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
但是,岳口人眼里没有汉江,只有襄河。要打鼓泅(游泳),就说去潭里,或是河里,“潭”指西边的荷花潭,“河”就是襄河;说岳口对岸沔阳的李嘴、郑场、毛嘴,不说“江对岸”,只说“河落边”。清代官方版县志中的岳口地图,标注的也是“襄河”。
襄河,汉江中、下游水道,自襄阳以下流经宜城、荆门、钟祥、潜江、天门,一直到沔阳、汉川地界,最后在武汉汇入长江。遥想上古时期,作为古云梦泽所在地的江汉平原,大泽深湖,水网纵横,襄河干流并无十分固定的河道及堤坝约束。岳口以北的天门全境均为襄河泽被之域,河水经常在岸左即北方洼地(主要是天门河流域到刁汊湖地带)呈漫漶状态。千万年间,汉水夹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在此沉积,“淤生其亩,广其田川”,云梦泽由湖盆而沼泽、由沼泽而平原,终形成河湖交错,阡陌纵横的江汉鱼米乡。
历史上天门之义河、西江、截河、三汊河、巾带河,乃至整个天门河,与襄河渊源极深。康熙版《景陵县志》载:“大河分一支自牛蹄口东迳陶溪潭、干滩驿出脉旺嘴为小河。”说的就是起自岳口上游陈家场附近的襄河支流——牛蹄支河。襄河在岳口上游分成南北两支,流经岳口的南支曾经仅为小支,北支即牛蹄支河古道,为干流,其在天门境内又曾分支多处。时人多知天南长渠,部分年轻人却不知天南长渠大段系牛蹄支河改造而来,更不知牛蹄支河曾是襄河干流,被当地人叫作大襄河。只是由于长时期的泥沙填积抬高了河床和两岸陆地,河道淤塞,北支式微,南支成为干流,成就了岳口的崛起。如今,襄河水仍在不舍昼夜地滋养着天门南部和东乡广袤的土地。
“襄”为古字,含上、高、举之意,史书里的“怀山襄陵”“云起龙襄”皆昂扬有为之辞,襄河的历史没有辱没这个好字。襄河,就是天门境域世代子民共同的母亲河。
二
从出生地天门城关搬到岳口,一定是老天对我的特别眷顾。作为人类一个渺小个体,在下农村以前,我及时地在襄河怀抱里学会了活命。
岳口的主街陈家巷子北连天岳公路,南接襄河轮船码头,后来打怪升级两次,先改称解放街,复改为解放大道。我居住并就读的岳口解放小学在解放街北端临近街口处。高年级设街西边的八德堂,紧邻岳口郊区生产大队-汉江一队5小队;低年级在街东边的陈家祠堂,和汉江一队6小队社员居住地相邻。岳口的郊区大队:上街是汉江一队,下街有汉江二、三、四队。命名反映了鼎革者的意志,如果由当地百姓取名,估计会叫襄河某队。
比起县河“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襄河绝对是“铁板铜琶”般的豪放气派。襄河儿女惯在风里浪里讨生活,岳口的男伢没有不会打鼓泅的。盛夏时节,河里像“下饺子”,只见黑压压的人头。有带车胎下水的,不为保命,只为好玩。车胎不是自行车、板车上那种猪大肠般细小的红色车胎,是可以承受两个人重量的黑色大马车胎,总有男孩仰躺在车胎上,顺着水流招摇而过。
从一码头到渡口,到轮船码头,再往下到二码头、三码头,是打鼓泅的集中地。这里有趸船,可以跳水,但河边水下都是石块,不好立足。且因主航道靠近岳口一侧,“迎流顶冲”,水势湍急,一旦下水游,至少是在下游百米开外才能上岸。所以很多人选择去“河落边”,打鼓泅的人坐渡船不用交过河费。对岸是大片沙滩,河床由浅入深,水流舒缓。
待到天色向晚,人们纷纷上岸起坡。“岳口十景”之一是堤上观赏的夕阳归舟,名曰“沧浪渔唱”,只是我们没文化,无意领略,只看到堤下的陈家巷子,一辆辆从天门城关回转的空载马车,一如凯旋的岳家军,“嘚嘚嘚”拐进堤坡下轮船站旁边的搬运站大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搬运和陆运合并组成的运输公司拥有板车马车一百多辆,牲畜近百头,是岳口一支十分雄壮的队伍。
八九月份上游山洪爆发,襄河变了脸,水位陡涨,河面比平时宽了不止一倍,浑黄的河水裹挟着上游的树木、草垛,甚至房屋架子、死的活的牲口等咆哮而下。有小学同学在作文里用“簸箕大的旋涡”形容水势,簸箕直径约有1米,非同样直径的脑洞,想不出这比喻。此原创金句经老师不怀好意地扩散,在我们中间经久不息地流传。
汛期打鼓泅的人就很少了,除了贪“浮财”的人。我们把打捞水中浮物叫“搂浪渣”,这是十七八岁以上水性高超的大人才敢做的事。像我们这样10岁出头的小屁孩没这个胆子和板眼,当然,看热闹是必须的。搂浪渣的人用长竹竿绑钉耙,或是绳子系上铁钩,看准目标下手,曾见到有人用钉耙拉衣物,待翻过来,赫然一具死尸。有特别好又难以弄上岸的东西,比如大木头、家具等,只能下水,那就要在下游好几里开外才上岸了。
三
襄河打鼓泅兼有玩耍和洗澡的双重意义,所以一般都是傍晚进行,男女老少齐下河。去荷花潭打鼓泅则是男孩子的专项游戏,多在中午时分去。
荷花潭在岳口西郊,是化肥厂背后从堤边一直向北延伸数里的数十个大小水潭的总称。历史上此处河堤多次溃口,洪水冲刷成这一溜数里长的水道遗址,所以这里的土质均是沙土。
沙土最适合栽种花生、红苕,还有瓜果,去荷花潭实际上是我们的专享套餐——以打鼓泅为中心内容,兼具摸鱼踩藕及沙田刨食的收获之旅。有藕肠子、莲蓬、菱角,有瓜果、花生、红苕,没有作业没有家务没有管教约束。在清凉的潭水里打水仗、饱口福,还有比这更爽的童年时光么?虽然也曾在摘地里黄瓜时不幸被抓了现行,游田示众,亲自怀抱赃物,亲自手拿话筒,供述作案经过。这是我少有的主角待遇和高光时刻。
那是肚皮远比面皮重要的年月,有限粮食与无限饥饿之间的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样尖锐,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过高规格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号召人们“低标准、瓜菜代”。我们被大人差遣去打个酱油,都忍不住要偷偷喝一小口,实难抵挡瓜田李下的诱惑。就是“瓜众”,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有时需要冒险。所幸襄河边的伢从来不缺冒险基因,我们在糊口填肚皮方面天生强悍,无师自通。
陈家祠堂拆除后,新建的解放小学东边有一条南北向水沟,北到岳口医院,南到小庙供销社生资仓库。这是汉江一队与二队的界沟,沟东为汉江二队卢庙队的大片瓜田——沟西众多小孩垂涎已久的地方。看瓜人守得严,大家谨按游击战“十六字诀”行事,瞅准机会,瓜田边飞快摆个系鞋带pose(其实都赤着脚),得手后飞快逃窜。
那时我们赤脚多,穿鞋少——既可延长鞋的寿命,又方便随时下水。解放小学旁边的这条沟曾布满了我的足迹,只要下雨,或是灌水浇地,就是我们捞鱼的机会。有年春节前夕,我在沟里逮到一条约两斤重的鲤鱼,这条鱼成为那年团年饭的主菜。若干年后,沟没了,那里开辟为居民小区,取名孝义新村。我家在那建了间私房,房址大致上就在我当年捉那条鱼的方位,尘世因缘真是个难以解开的迷。
四
鱼米乡再贫瘠,也不会“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那时的鱼真多。有段时间我住在化肥厂,食堂就在荷花潭边,工人们吃了饭就舀潭水洗碗,残菜剩饭散落水里,不断有鱼上下翻腾抢食,雪白的肚皮在水里闪过,撩得人心痒难耐。弄个竹竿系上钩线,随便钩点饭粒或面坨,放水里就有咬钩的,一拉一条,绝少落空。这是我钓鱼生涯的开端,
后来就不行了,化肥厂的工业废水不断朝潭里排放,有年冬天,厂后面方圆几里的水潭里,鱼儿纷纷浮头,捞上来的鱼吃起来都有一股氨水味。钓鱼越来越成为一门技术活,只有“活鲫鱼老头”出满勤站满天,风雨无阻。全镇小孩都认识这位岳口惟一的职业钓者。他所有的钓具都是自己设计或打造的,比如鱼钩,市上售卖的鱼钩都是倒钩向内,他的鱼钩却是倒钩向外。我曾经高价找他买过一枚鱼钩,业绩并不好,鱼似乎认人不认钩,老头另有不传之秘。
钓鱼专业性太强,又费时间,所以我们捉鱼多采用更简单直接的办法,如在流水沟里埋下“竹háo子”——一种“请君入瓮”式的捕鱼工具。最粗暴的,是将水沟的一段用泥巴两端筑坝拦死,然后用脸盆将水舀干,竭泽而渔,纯体力活。

童趣
如果要向一个水塘的所有鱼类下手,则须众多狐朋狗友一起下水,这叫“反坑”,一个杀气腾腾的名称,让人想起反动、反xx,还有“薛刚反唐”等嚇死怕人的字眼。
“反坑”的基本工具是“哈搭子”,由一个弯弓样柳条框和网兜组成的撮鱼工具。买是买不到的,只能自己做。关键工艺是网的防腐处理——用猪血浸泡揉搓后晒干,如此这般反复两三道,使猪血里的蛋白质渗透进渔网纤维里,变性凝固,拒腐蚀永不沾。
我们下水后一字排开,用“哈搭子”在水中齐头推进,要不了几个来回,塘水就混浊不堪。鱼儿纷纷浮头,鲫鱼则扎进水底的泥巴里,都逃不脱被捉的命运。那几年,我们“反”遍了上街周边几乎所有的大小水塘。
无论是捉鱼踩藕还是采摘瓜果,都是为了糊嘴。每个小孩都能从大人们精打细算的日常行为中、从父母发工资前几天的愁眉苦脸中、从兄弟姐妹看到吃的就炯炯发光的眼睛里,感觉到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危机。所有的创收都是小伢们自发的行动。在郊区生产队刚收获过的田地里,总会有小伢们忙碌的身影,我们挖地三尺,很耐心地翻找没有收干净的萝卜、红苕、花生、洋芋等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
除了吃的东西,其他可以贴补家用的东西也在我们的“狩猎”范围内。襄河上游紧挨着化肥厂的是岳口电厂,烧煤发电,于是就有煤渣可捡。
我捡煤渣是团队出动,带着弟弟妹妹,推着自制的独轮车。隔一段时间(大概半小时),电厂工人就用铁皮车将烧过后淋了水的煤渣推到堤上的煤渣场倾倒。我们一拥而上,高举锄头之类的挖刨工具,将冒着热气,闪烁着暗红火星的煤渣刨到随身携带的铁篓或竹箢子里,再提到一边去细细分拣。这是火中取栗的激烈战斗,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在一次争抢中被倾泄而下的滚烫煤渣灌进了套鞋里。手忙脚乱好不容易脱下套鞋,一只脚已烫成红烧蹄髈,不堪回首,不提。
岳口伢很多都拥有一辆自己制造的独轮车。一个滚珠轴承当车轮,一根铁棒作车轴,两根一米多长的木棍当车帮,钉几块木板就成。这是我们讨生活的基本工具,除了捡煤渣,买米、买煤、地里刨食都要靠它运输。去下街多是买米买煤。庙巷口的红卫粮店和更下游的煤场都紧靠堤坡,大宗物质的仓库或卖场多设于堤坡旁,方便水路运输和转运。堤外对着红卫粮店的,就是二码头和三码头。
五
下街的废品收购站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牙膏皮3分钱一个,猫狗皮毛(罪过罪过!)、废铜烂铁、挖的半夏等中药材,小伢脑壳想得到的可以来钱的事,都会想方设法去做。
比如养蚕,通常是将蚕卵(产在纸上的蚕卵)揣在贴身衬衣的表荷包里孵化,上课时,乘老师不注意就偷偷拿出来,看有没有蚕孵出来。待到孵出小蚕,放纸盒(比如医院装过针药的盒子)里,放学了要去摘桑叶,岳口医院旁的渠道两边栽满了桑树。桑叶要干燥以防蚕宝宝拉稀,纸盒要盖好以防蚊虫。小本经营不容易,蚕茧也卖不了几个钱,但绝对是有技术含量有获得感的光荣创业经历。
解放小学操场边是牛马交易所,女伢割草卖,一篮草可以卖1到两角钱,男伢则放牲口。总有小孩在牛马场晃荡,等待商机。有一次,给河南贩子放毛驴,其他小伙伴都是牵一头或两头,我牵了三头,盖因带着弟弟,好歹凑了个人头。一头驴两角钱,三头6角钱,一单大生意。我们把驴子牵到上街堤外的沙窝,把缰绳一端的钉橛钉在堤坡上,然后自由活动,人畜两便。
襄河在岳口上游一段是南北流向,到了沙窝突然一个大转折,向东而去。航标站、船厂、汽车轮渡码头都设在这里,滩涂开阔,好玩的地方多,这是我们的免费游乐场。河岸上倒扣着修理中的木船,总有工人在那忙活。因荷藕然在回忆文中讲,他小时候去沙窝,主要是“捡抓钉”拿到收购站去卖。虽然船厂抓钉都是有用的,但“捡”不是拿,岳口伢有底线。
沙窝西边是大片防护林,堤防管理段的护林老头总在那儿溜达。有小伙伴和这老头是老朋友,他们去树林里捉“铁牯牛”,铁牯牛吃树叶,三五个铁牯牛能在老头那儿换1分还是两分钱。我不做这生意,宁可爬树上找“知yǐ zì壳”,就是中医先生称为“蝉蜕”的东西,拿到收购站换钱。
管理段隔壁就是岳口剧场。只要有演出活动,精力过剩的青少年男女们就早早地向这儿聚集,堤坡上到处是三五成群游逛的人,我们散散漫漫坐在堤坡上,等待机会。票是没有的,看有没有可乘之机溜进去。待到开始检票进场,有票没票都往门前涌,少不了年轻女伢被人揩油后的惊叫与喝骂声,成为岳口堤坡下惯常的夜景。
岳口的热闹场所都在河堤上下。比如镇委会前的土台,地位相当于城关的工人俱乐部,大型集会、庆典多在此举行。堤坡就是天然座席,居高临下不愁视野被遮挡。印象中有个民间歌唱家,总是唱一首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其实他好像是五金公司的,只能献扳手。还有儿时伙伴郑和平的哥哥,我们喊双喜哥,方木社的,拍渔鼓筒子唱“道情”,是岳口一绝。对镇委书记曹克及岳口大小“黑帮”的批斗会也在这里举行过多次,这是小伢们的节日——凑热闹、看稀奇,随便起哄,黑帮们又不敢有任何反抗。至于镇委会隔壁的电影院,建成后恰逢WG,一直无用武之地,直到70年代中后期电影大规模开禁,才热闹了几年。
六
16岁下农村以后,岳口于我,就只是个探亲和歇脚的地方了。71年还是72年冬,我被派到岳口修堤坡,搬了几天石头,这是我惟一一次以建设者身份为岳口作贡献。只是很快就被大队召了回去,快过年了,宣传队要排节目。还有就是作为农民工,在襄河坐驳船经沙洋上枝城修铁路,以及去荆门修水泥厂,人和行李在底仓挤成压缩饼干,不是什么愉快经历。

今日的岳口码头一派田园风光
那几年,母亲调到了岳口东郊的工农兵小学,校址在纯阳阁,很偏僻的地方。我少不了一次次在从正街到纯阳阁的岳口大堤上往返。纯阳阁附近的堤内戳着几个像蒙古包的硕大油罐,这是岳口的石油仓库,堤外是专用的石油码头,这里人烟稀疏,和乡下没啥两样。
再后来外出读书、工作,都是经汽轮码头过河回岳口。上世纪末终于可以直接经岳口汉江大桥抵达了,现在则是从随岳高速岳口收费站出来。不知这是意味着岳口交通的发达,还是岳口地位的边缘化。据说岳口现在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和全市惟一的“省级文明镇”,应该为之高兴。
好像所有在外地的岳口人回岳口,都会去堤上看看。如今的岳口大堤,杨柳青青,碧草连天,间或看到堤坡上悠闲吃草的牛羊。码头日渐凋敝,船舶稀少,街上早没了马车雄赳赳的影子,即使是盛夏,河里也不复见当年人头攒动的喧闹景象。
如果不是方志中白纸黑字的记载,真不敢相信,岳口的正街曾经是堤街。当年“九街十八巷”,最热闹的街都傍堤而建。志书记载,岳口曾有4关、6码头、16处会馆书院、30处庙宇,另有“岳口十景”闻名遐迩。“通衢慧贾,人烟日渐辐辏;瓦屋鳞次,估舶衔尾”。镇上处处亭台楼阁,襄河日夜帆樯如梭,这是何等的盛况,何样的气派啊!
这些我们都无由得见,上辈人是最后一代的见证者,他们也大多伴随着“小汉口”的传奇远去。我们生长在一个历史的断层里,留给我们的,是从小在河上河下扑腾的碌碌无常,以及偶尔撞击心头、祸福莫辨的小确幸。
遂想起天门曾有一首和我们这代人同时期诞生的《襄河谣》,专咏自然,不见商衢。优美的旋律因被那首《洪湖水浪打浪》借用而天下流传。民间俚曲与时代壮歌结缘一瞬,擦肩而过,看似有情却无情。
惟有襄河滋养万物,奔流千古,见证着两岸的沧桑轮回,和一代又一代襄河儿女的苦乐年华。
《襄河谣》歌词:
襄河水哟黄又黄,河水滚滚起波浪。
年年洪水冲破堤,襄河人民遭灾殃。
窟窿多哟浪涛狂,河岸浑身是脓疮。
冲坏了多少庄稼地,冲走了多少茅草房。
笑嘻嘻,喜洋洋,打好河堤唱一唱。
嗓子越唱越响亮,襄河变成百宝箱。
襄河宽,襄河长,襄河喜得日夜忙
人人跟着襄河唱,襄河是个好家乡!
注《襄河谣》:原襄阳军分区文工团创作员吴群先生转业到天门花鼓剧团后,于1950年借鉴天沔小调《月望郎》的音乐元素,创作了歌曲《襄河谣》。又:明清之际就有俚曲《玉娥郎》流行。蒲松龄曾将该俚曲编入话本《磨难曲》中,话本主角名张鸿渐(《聊斋志异》有《张鸿渐》篇目)。《玉娥郎》与天沔小调《月望郎》有无关联,值得探究。
主要参考资料:清钱永修等编《景陵县志》(康熙版);胡忠义等编《天门水利志》(1999版);陈玉祥主编《岳口镇志》(1990版)。
庚子年仲夏 修订旧作于北京玉渊潭
解智伟诗歌作品链接:
那片帆丨英雄不倒即战旗
——给谢力军
作者/解智伟

他把一所助产学校
办在天上
在云里接生了舂天的雨滴
河流带来的绝不仅是水
沧浪分娩出
痛与惊喜
遍插茱萸的九月九
他在一篇篇散文里
寻找多年前走失的兄弟
他用一生在等一个人
他用整片海喂养一条思念的鱼
任凭沧浪之水
在脸上哭泣
每一条河流
都无法把波涛忘记
只是很少人知道
翻来覆去的《沧浪之歌》
写的是怎样的主题
与水争命的往事
都在他悲欣交集处落笔
他从《水经注》里
开掘出一条河
流经他故乡的土地
总有一片帆
沿着他的脊梁升起
翻飞如旗
他把江河的信仰延伸到海里
他打开全部的天空
收集鸟一一飞过的痕迹
他喜欢唱《鸿雁》
他想用翻山越岭的歌声
唱一个人的归期
他也喜欢酒
他要用沧浪踉跄的醉意
醉倒在影子里
与自己合二为一
一起回到古代
那一年,风高水急
火烧连营八百里
赤壁,一面红色石帆
悬挂了千古悲喜
历史在跌跌撞撞中站立
不负苍生泪
沧浪之后,英雄不倒即战旗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