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齐诗歌美学基调浅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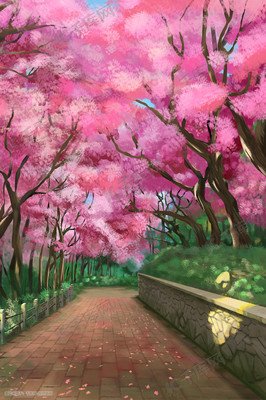
认识张国齐,是2025年的春天。
这是一个注定是与诗有缘的春天。诗人蒋文辉(岛子)近年来诗兴大发且佳作迭出金句迭出。不知是诗情浓了春色,亦或是春色浓了诗情。一次七嘴八舌谈诗论文的小聚中,一位面相清癯的诗人,言谈中对诗歌的内在美以及当下诗坛现状有相当精到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询之,此网名为齐安乡人的中年人,大名张国齐,年轻时戍守边关,退役后在卫生系统任党务工作者。
这让我大为惊奇:党务工作者公务繁忙,难得有诗情画意盘旋于胸臆间,可这张国齐,一直痴情于诗歌和诗歌创作,公务之余,笔耕不辍。所作诗歌,题材广泛,既有对家国大事的关注,《走出去就是一种选择》中,诗人穿过时空隧道,尽可能身临其境地抒发心灵深处对改变历史进程辉煌的虔诚:
我知道,/重走一遍红军路/我还是走不成红军/就像鹦鹉,/学而时习之/我还是一只学舌的鹦鹉/但是走出去,/就是一种选择/走上一回就是一种朝圣/去聆听那路上的风雪历史/去捡拾那些遗失的声音/走出去就是一种决绝/为的是与昨天的自己告别/尽管走上一回,/也不可复活苦难辉煌/走出去,/与其说是寻找/莫若说,/为唤醒自己/为了明天,/走出逼仄的现在/走出去/沿着三月的春天

张国齐的作品中,也有对生养抚育其生命故土、先贤虔诚深情的歌咏。《张家榨之谜》,是一首值得细细咀嚼的作品。这首诗因诗人倾注其中的浓烈真情,读来让人动容:
……1960年某个黄昏,/母亲怀抱饥饿待毙的我在村口守望,/终于守望到归家祖父的小半碗米糊,/那可是出苦力的祖父一天的食物呵!/不足三岁的我,/少不更事,/岂知其中艰辛。/我,每天就是靠祖父的那口粮活命,/而祖父那时啃嚼巳榨尽油的一块菜籽饼。/若干年后,/祖父不再魁梧高大,/而是柱仗佝偻而行的瘦弱老人,/是我,是生活,/是岁月把祖父压榨殆尽,/压榨回村湾一座小小坟茔。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乡愁二字可以浓缩的真情,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呕心沥血,是一种因崇高所牵引的心灵的膜拜。
张国齐诗作所涉题材非常广泛。但无论叙写何种对象,成为有韵律的诗句呈现给读者时,最动人之处,并非写物状形的细腻入微的立体感和诗人试图与读者互动的代入感,而是诗人超脱出叙写对象的那一份似有还无的洒脱。这如其说是一种写作状态,毋宁说是一种悟透世相从而产生的一种难得的空灵,一种似有还无的时而蛰伏时而怦然的心灵深处的诗情画意。这在《秋夜听蟋蟀》、《诗,是一株暗夜生长的植物》、《那年,湖畔的桃花》等作品中可见其端倪。
在张国齐众多的诗作中,给我触动最大的当是他涉及“秋”的作品。
以秋天为题材或“引子“的诗歌高手,数不胜数。唐代,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人:一是杜工部杜甫,不愧诗圣之誉,他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如一支伸缩自如的变焦广角镜头,将峡江的秋色秋情细致入微地让人入眼入脑入心。
再一位是自号“香山居士“的白居易,他那首《琵琶行》中秋色秋意的叙写,真个是让人拍案叫绝:”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以秋为药引,借”琵琶女“之酒杯,浇”江州司马“自己胸中的块垒,的确是高手。另一位是刘禹锡。他《秋词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上九霄。”从杜甫、白居易对“秋”“悲”的基调中跳将出来,给一向有凄凉之意的秋,注入了如诗人自身际遇不成比例的万丈豪情。
张国齐《秋时遐思》、《立秋》、《抚弹一江秋水》,都是以“秋”为叙写对象的。这三首同题材却不同立意的诗,是窥视张国齐诗魂的窗口:
孤寂的人兀自怅惘/相思的人天涯断肠/秋风秋雨涨满李清照词池/小楼昨夜是李煜千年酒酿/一只孤雁飞进瞳孔/将我心的柔软撞伤/一只孤雁飞出瞳孔/拽出多少异样目光/举首极目 寥廓江天/秋风萧瑟 落叶金黄/有一只孤雁掠过……《秋时遐思》
其后,是“飞进瞳孔”的那只孤雁向“目的地”飞行的“跌宕际遇”,从而将“秋时遐思”中的“遐思”做了形象的诠释,也从而摊开了诗人于人生途中奔波的一言难尽的自豪和一些儿苍凉。
梧桐兼细雨,/点滴生凉意/不经意间,/蝉蜕了,/天秋了/……/一朝醒来 ,/投目曾爱的人/不经意间,/爱没了,情深了/……攀爬人生坡谷,/未敢言沧桑/不经意间,纵壮心不已,/鬓发霜了/向晚枯坐,/……河畔歌吟,/渔舟唱晚/不经意间,岁月老了《立秋》
这可以看做是一首人生经过认真跋涉之后小憩的真实写照,有些许疲惫,有些许过来者的感悟,有“人身易老天难老”的无奈和妥协。还能让人联想到“酒酣胸胆尚未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不甘与期望。
披苏轼一蓑烟雨/乘李白一叶扁舟/携竹林一干闲人/寻桃源一处入口/荷钟子期一担柴禾/……沉浸一曲高山流水/贵妃腴美,乃一骑红尘/拾遗补阕,立一根骨头/仄入西厢,一见钟情/岁月如歌,一叶知秋/生活琐絮,一地鸡毛/子在川上:一声浩叹/……小说人生,/一袭爬满蚤子的华美长袍/诗意栖居,沉吟汨罗江怎禁一夜白头……《抚弹一江秋水》

这是张国齐一首立意颇为新奇的作品。诗人将思绪穿过重重历史云烟,使其“抚弹”的指法,刚柔并济,时而芒鞋竹仗,一副探寻历史桃花源的闲适;时而高山流水,知音在侧;时而梦回大唐,抚额长叹,“一骑红尘妃子笑”,“辗转峨眉马前死”;时而龙舟竞渡,汨罗江惊天动地的一跃,荡起洪钟大吕的回声……
秋,秋声,秋色,秋实,秋梦,秋思,在张国齐笔下各擅其美,如一群“秋”的美姬,一个个风姿绰约,一个个顾盼生姿——诗人塑造秋之美的形象思维,可谓思鹜八级,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给人以收放自如之感,很难得。
如果实在要从诗歌流派上给张国齐的诗定个调子,愚以为可入“唯美派”之列。纵观张国齐的诗作,无论题材如何变化,细腻的描摹功夫,意象构建美学基点的定位,句式参差而不失彼此照应的节奏感,主观咏叹情感审美旋律的配置,都难能可贵地达到了相对和谐的统一。
要全面系统地从诗学理论的高度品评张国齐的诗,非千字文可为,当需相当的学养修为。老朽不揣浅陋,写这读后感,定是挂一漏万,聊作粗浅评析,以求教方家罢。
2025年3月29日于后湖
———————————————————————————————————————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彭建新,1947年生,武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2003年任武汉市文联副巡视员。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前,创作以诗歌、散文、随笔为主,亦涉猎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创作;1995年起,开始了以武汉城市发展为背景的地域风情长篇小说创作,至2003年,已创作并出版系列长篇小说《红尘》三部曲:《孕城》(34万字)、《招魂》(50万字)、《娩世》(40万字)。另有《凝固的记忆.武汉老街巷》、《模糊的背影.武汉老行当》、《武汉老街巷》、《武昌老街巷》、《人间情话.彭建新散文随笔选》等多部,迄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800余万字。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