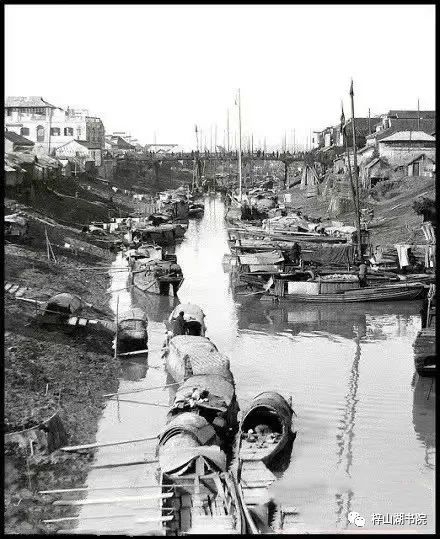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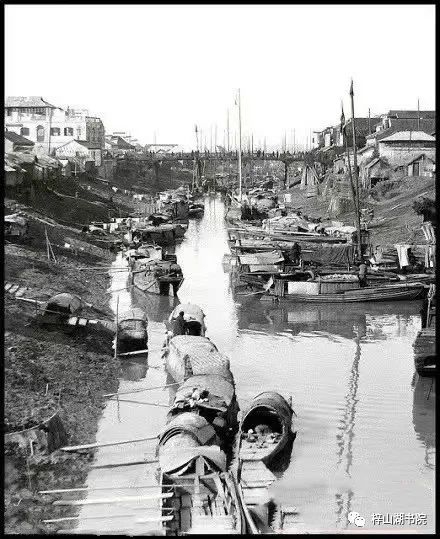
3
与白脸太君撕破脸是装盐那一回。那一回打老河口装盐走沙洋。中间的货舱漏了,舱底渗进的河水淘了压在舱底的两个盐包。从头天一大早直到第二天下午,父亲才发觉漏舱了。父亲忙问祖父咋办?祖父叫父亲拽出两个湿淋淋的瘪瘪的草包给白脸太君看。谁知太君变得恁不通人情,他的白脸翻成红脸又叠成青脸,一口咬定盐是父亲偷了。
父亲辩白说:“明明是舱漏了水淘了盐,太君不信去舱里看看。咋说是偷了?”白脸太君叭地一巴掌扇在父亲的左脸上。父亲感到左半边脸皮给烙了似的火辣辣的发麻。他用一只手捂着脸跳进货舱里,伸出另一只手指头蘸了舱里的渗水咬在嘴里含着对白脸太君说:“太君不信尝尝?这舱里的水咸得发苦!”白脸太君又朝父亲的右脸扇了一巴掌。父亲觉得嘴里含满了涎水含不住了便呸地啐出来,原来不是涎是血。他用手背使劲一抹嘴角的血,又说:“太君不信拿锅来熬熬舱里的水,保准熬得出盐渣子来。”
这时祖父见势头不对早抢过了母亲手里的舵打舵靠岸,并大声叫唤前头船上的鸭屁股。鸭屁股一招呼,所有的船都靠了岸,船老大们纷纷跳到岸上朝祖父的船跑过来。这一下糟了!各船上的太君也都跳上岸,叽哩哇啦地吼着逼赶船老大们上船继续航行。白脸太君见状大怒,他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把父亲拽到坡上绑在河边的一棵杨树上。鸭屁股和船老大们就吼起来,搡着攘着要冲上去解救父亲,太君们纷纷端起枪呀呀地叫着把枪刺比划着堵住他们。太君们很惊讶,他们不知道船老大们早窝着一肚子火烧得难受。他们的倔犟脾气发作了,不管他刺刀是铁打的胸膛是肉做的,一个劲朝前挤着,逼得太君们连退几步。这时,祖父抚着一条软塌塌垂着的瘸胳膊过来,象一只断臂螳螂踉跄着挡住了鸭屁股他们。祖父突然明白了太君的刺刀决不会退缩,他要制止这场血灾!

他浑身大汗淋漓急得牙巴骨乱锉着挤出断续地嘶喊:“让他们捆……让他们去……惹不得呀……忍住……忍住呀!”他知道应该牺牲儿子的皮肉来保住儿子和大伙的性命。天色急忙黑下来河林子阴森森的。刚才吓得乱哭乱嗥的艄婆子们和娃娃们都屏住了呼吸,不安地躲在凉棚里朝岸上偷望。太君们在河边烧起一堆篝火来拷问父亲。白脸太君没有鞭子也不用枪托打人,他爱惜他的枪,每天擦几遍藏在船头他的睡舱里不轻意拿出来。他就用他的两扇巴掌交替打父亲的左脸和右脸。父亲的脸立刻肿起来,肿得象个猪嘴巴拱得老高。
母亲吓傻了眼。她咋也没想到白脸太君变得恁凶恁毒她竟一时以为他是另外一个人。当她愣过神来认清他确实是俩娃子的亲密朋友白脸太君时,她赶紧抱着长兄拉着大姐上坡,不顾祖父的阻拦,强行跑到白脸太君跟前跪下。她叫娃子们也学着她跪下,但大姐和长兄颇有傲骨都不给打他们爹的太君下跪却跑去抱住父亲的腿哭。母亲指望错了。白脸太君翻脸不认她也不认哀容惹人柔肠寸断的长兄和大姐。他烦躁地挥挥手说:“小孩哭啦哭啦的太君头疼!”他嫌娃娃哭噪他的耳朵。大姐和长兄也确实会哭,啼声象杀猪象夜里叫春的猫似的听来疹人。不过太君总算没再扇父亲的耳刮子了。他也气得汗颜,帽子歪了脖子上的纽扣扯脱了呼哧呼哧直喘气。母亲见白脸太君上船找水壶喝水去了,忙立起来对父亲说:“太君不讲理俺们挺不过去,您就照他说的认啦盐是偷啦再看他咋说?”父亲跺跺脚把脸扭向一边不吭声,他也不能吭声,他的牙被打落了两颗含糖块似的含在嘴里没吐出来。这时白脸太君喝了水擦了脸又跳上坡来。他瞧瞧捆在树上的父亲,瞧瞧母亲长兄大姐和冷冷地立在一旁的祖父,又瞧瞧对峙着的那群船老大和东洋兵。他的眼光又凶狠起来,逼到父亲跟前。母亲也使劲瞪了父亲一眼催他开口,她见父亲不睬她,便自己硬着头皮朝白脸太君很惭愧的笑笑:“俺问俺男人啦,他认啦盐包不是给水淘啦是叫他偷啦。他说他好吃好喝偷盐换酒换肉米西米西啦。太君肚量大大的他的心眼小小的。”白脸太君点着头很仔细地听母亲说完,便仰着脸闭着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满意地搓搓手掌绕到树后头给父亲松了绑。拷问出乎意料地结束了。白脸太君和所有的太君都回到船上去了。父亲用手捧着吐出了嘴里的两颗牙。船到沙洋卸了货。白脸太君见父亲拱着的猪嘴不消肿,牙龈出血,便塞两张纸币在长兄的小手上,叫父亲去治病。父亲接过那钱,却扬到河里打漂漂给白脸太君看,转身去找母亲要了钱上坡找牙医。父亲被打落了一颗上门牙和一颗下门牙。他把手里攥着的两颗牙递给医生,问这牙还能不能让它长到嘴里去?医生说这牙没用了但可以镶金牙。苦力的干活自然没钱买金子,于是父亲就让门牙豁着象个落了牙的糟老头,一张嘴说话便露出豁洞,象个写歪了的“8”字。自小就不多话的父亲由此愈加羞于启齿。

父亲成了个豁巴齿还把那两颗打落的牙包在纸烟壳里藏着。直到后来白脸太君走了,他见那两颗牙都发了霉才扔进河里。母亲忙乎了几天。她把中间货舱里的盐水都舀起来留着,盛满了大桶小桶大盆小盆坛坛罐罐。她在河滩上架起铁锅熬盐。熬出的盐末子细细白白的象洋面粉,装了满满一布袋子,还给了鸭屁股的艄婆子一大钵。那艄婆子也来帮忙熬盐,故意阴阳怪调地喊:“哟——如今这盐价可不便宜!没听说张自忠的队伍掏大价钱到处买盐?”母亲便接过话茬子大声嚷嚷:“俺这盐甭掏钱!是俺男人的两颗牙换的!”白脸太君明明看见了母亲熬盐也听见了她嚷嚷,但他装作没看见没听见。母亲不再答理他,也断然拒绝他对娃娃的恩赐。大姐和长兄也怕他躲避他再也不敢去船头玩耍,有时在船舷、桅下撞见他,便吓得哇哇哭着掉头飞逃。
但母亲仍在暗地里关注白脸太君的举动。她发现他很寂寞,一副丧魂落魄的鬼样子。她见他咋就也不做操也不跑步了,却会吸烟会喝酒了。她惊讶他那酒量竞比祖父还大,不分白天黑夜地昏喝。他喝醉了就抱着那根长笛疯疯魔魔地吹,却又吹不成个调儿,忽高忽低时断时续的,母亲听来很古怪很不吉利。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钱鹏喜,笔名鹏喜、金戈、羊角,自由撰稿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武昌理工学院教授。曾任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芳草》主编、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主要著述有长篇小说《河祭》等5部,长篇报告文学《龙马负图》等2部,散文集《梓山湖笔记》等4部,《鹏喜中短篇小说》1部。多次获得湖北省、武汉市文学奖项,多种作品入选《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和《武汉文艺精品丛书》。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