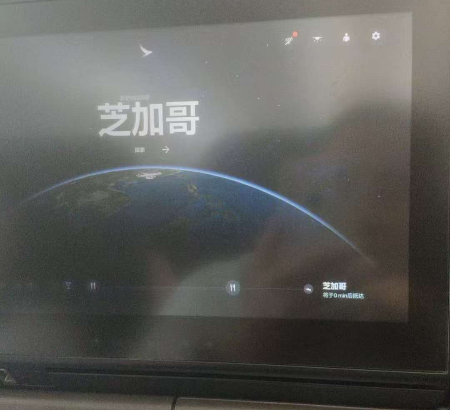
同机抵达的乘客
那些擦肩而过的、短暂同行的、或是相伴许久的人,都在时光的车厢里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2025年6月9日这一天,我从香港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姑娘家探望外孙,这场跨越重洋的旅程中遇见的乘客,便成了我记忆里格外鲜明的篇章。
香港的清晨带着夏日特有的湿润与暖意。天刚微亮,我便收拾好行李,窗外的维多利亚港还笼罩着一层薄雾,几艘早班船正缓缓划过水面,船尾拖出的波纹在晨光中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女儿前几天在电话里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爸,两个孩子天天念叨着外公外婆,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时,老伴举着一件小童装凑到我面前,眼眶微微发红:“你看,这是小外孙去年生日时穿的衣服,现在估计都短了一截。时间过得真快,上次视频他还只会喊‘外公外公’会一点中文,现在说不定都会背唐诗了。”我接过衣服,指尖触到柔软的布料,仿佛能感受到孩子温暖的体温。想到马上就能见到姑娘一家人,尤其是两个可爱的外孙,心里就像被暖阳照耀着,满是期待与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漂洋过海,内心满是兴奋与好奇。中午十二点,我与老伴跟着人流,走进香港赤鱲角机场。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不同语言的交谈声、行李箱滚轮的滑动声混在一起,透着一股热闹的气息。国泰航空CX806航班的登机口前排着队,大多是拖家带口的旅客,也有背着巨大登山包的年轻人。走进经济舱时,一股淡淡的航空油味混着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头顶的阅读灯亮着柔和的光,乘客们正陆续找座位,有的在摆放行李,有的在和邻座小声打招呼。

广播里传来空姐甜美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程13845公里,预计飞行14小时39分……”我找到第三排C座坐下,刚把背包塞进前排座椅下方,就注意到第一排A座的老妇人。她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身上穿的黑色背心是丝质的,领口有点松,能看到她后背大片的彩绘。那是一只展翅的老鹰,和美元上的图案一模一样,鹰嘴叼着的字母“E Pluribus Unum”我不认识,但那鹰嘴画得特别锋利,像是用刀子刻出来的,翅膀从肩膀一直延伸到胳膊,鹰爪紧紧抓着臂弯,颜色很深,看着让人有点不敢靠太近。她正低头整理手提包里的东西,手指上戴着好几个银戒指,动作慢悠悠的。
突然,老妇人的一枚银戒指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弯腰去捡,却因动作不便差点摔倒。我连忙起身帮她拾起戒指,这才发现她手指上布满了老年斑。“谢谢您,”她抬起头,眼神温和,“这枚戒指是我丈夫四十年前送的,他去年刚走,我现在要去芝加哥看儿子,把他的骨灰撒在密歇根湖畔——那是我们年轻时约会的地方。”我这才明白,那只老鹰或许不仅是纹身,更是她对逝去爱情的纪念。

正前方的小伙子大概三十多岁,脸上有些浅浅的麻点,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他一直没抬头,平板电脑放在膝盖上,屏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他看得很专注,眉头时不时轻轻皱一下,右手食指会跟着文字慢慢滑动。有一次飞机轻微颠簸,他伸手扶了一下前排座椅,我瞥见他手腕上戴着一串木质手串,颜色磨得很亮。
中途,小伙子突然接到一个越洋电话,用中文焦急地询问:“妈,爸的手术顺利吗?您别担心,我这边项目一结束就马上回国……对,您每天把他的康复视频发给我看看。”挂了电话后,他久久望着窗外,眼神里满是牵挂。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芝加哥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这次是临时出差,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国内生病的父亲。那串木质手串,是他离家时母亲亲手为他戴上的。

旁边的黑人女孩让我印象最深。她的皮肤黑得像墨,笑起来时牙齿白得晃眼。头上梳着细细的辫子,一条一条紧紧贴在头皮上,中间的辫子竖起来,周围的辫子绕着它盘成一个圆,远远看过去,就像戴着一顶精巧的帽子。我想起小时候在课本里见过屈原的画像,头上的冠冕和这发型竟有几分相似。她时不时会对着小桌板上的镜子整理辫子,手指灵活地把散落的发丝掖进去,嘴里还轻轻哼着什么调子。
当她看到我盯着她的发型出神时,主动对我笑了笑:“先生,您喜欢我的发型吗?这是我妈妈教我的,她是尼日利亚的发型师。我现在要去芝加哥读大学,学的是国际关系,希望以后能促进中非文化交流。”说着,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她和家人都梳着类似的发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还告诉我,她哼的是一首尼日利亚民谣,是妈妈在她临行前教她的,说是听到歌声就像妈妈在身边。
飞行途中,空乘推着餐车过来时,整个机舱飘起食物的香味。老妇人要了一杯红酒,小口小口地喝着,眼睛望着窗外的云层,不知道在想什么。黑人女孩拿出自己带的小零食,还分给我一块裹着椰丝的巧克力。那个看英文的小伙子要了杯黑咖啡,喝完后又继续看他的平板,中途只起身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时还对空姐说了句“Thank you”。
我和老伴分着吃那块巧克力,椰丝的香甜在口中弥漫开来。老伴突然轻声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坐飞机吗?那时候你刚升职,带我去北京旅游,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还是你一直握着我的手。”我握住老伴的手,她的手指有些粗糙,却依然温暖。我们相视而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时光。
透过舷窗,云层有时像堆积的棉花,有时又像被风吹散的薄纱。看着身边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看电影,有的在小声聊天,忽然觉得人生真像这趟航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却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度一段时光。就像那把伞的比喻,生活里有晴天也有风雨,重要的是能像这些乘客一样,各有各的活法,却都在认真地往前走着。爱因斯坦说人生像骑自行车,其实在这14个小时里,我看着身边的人,忽然觉得更像这架飞机——要穿过云层,要经历颠簸,但只要朝着目标飞,终会到达想去的地方。
飞机降落在芝加哥奥黑尔时,夕阳把跑道染成了橘红色。乘客们起身拿行李,老妇人后背的老鹰图案在走动中一晃一晃,黑人女孩的辫子在灯光下闪着微光,小伙子把平板收进包里,终于抬起头,对我笑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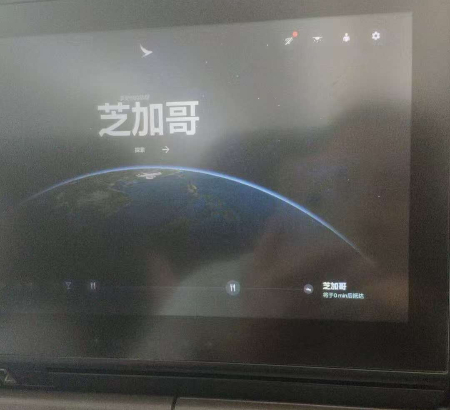
我走出机舱时,远远看到姑娘一家在出口处向我们挥手,两个外孙蹦蹦跳跳地喊着“外公外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无论是陪伴多年的亲人,还是短暂同行的陌生人,都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跟着人流走出机舱,心里想着,或许以后再也不会遇见这些人,但他们就像这趟旅程里的风景,让我知道生命的路上,总会有不期而遇的精彩,值得为每一次相遇停留,为每一片晚霞心动。
看着机舱里这些形形色色的乘客,我不禁想到:人活着,就应该像一把伞,晴天时优雅地收起,不张扬;风雨来临时从容撑开,不退缩,既能承担起责任,也能控制好情绪。爱因斯坦说过:“人生就像骑自行车,只有不断前行,才能保持平衡。”生命的精彩,在于每个当下都能心怀热情,点燃心中的火种。
愿我们都能带着对生命的热爱与思索,在未来的日子里,不仅为了抵达目的地而努力,也能为身边的美好停留,为一朵花开而欣喜,为一片晚霞而感动。让每一次相遇、每一段旅程,都成为生命中珍贵的记忆。
2025年盛夏写于芝加哥
作者简介:廖生斌,男,湖北省武汉市人,1980年11月入伍,团政委任上退出现役。1999年转业至武汉海事法院,现已退休。喜欢写作,习惯品味生活。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