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的父亲闵之珠(乳名闵传善)出生于1924年农历十月二十日,辞世于1991年农历七月初三,享年67岁。今年是我敬爱的父亲驾鹤西去的第33周年,也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
今年(2024年)七月初三,我和家人如往年一样在父亲的祭日回乡为父亲祭祀时,我突然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但苦于笔力太钝,水平太低,加之身体欠佳(做过头部开颅手术且眼睛染疾不能多用眼),虽有此想法,却一直未敢动笔,直到今天翻开日历,我惊慌地看到离父亲诞辰日只有二十天,我再也坐不住、等不及、拖不下去了,于是我在诚惶诚恐中鼓起勇气提笔作文,我想不管我写的怎么样,也算是我对无限敬爱无比怀念的父亲的一片深情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这世上最疼爱我、最关心我、最在乎我、最理解我的人。他的纯朴善良、诚实守信的品质,他的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的个性,他的礼貌待人、与人为善的性格,他的办事认真、敬业负责的精神,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情操,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是我人生路上的动力和源泉,就像他的乳名“传善”一样,他留给我们的家风就是:忠厚传家,善良为本。

父亲生前与家人照的一张全家福(前排右二)
父亲的一生很普通,充满坎坷与平凡。但是他那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之中蕴含着杰出,他那种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之中深藏着伟大。他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出生时家里有薄地十几亩、房屋三间、耕牛一头,耕地务农的配套农具比较齐全。父亲兄妹三人,他是长子,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祖父祖母都是靠务农为生的农民。父亲少年时期除读过三年私塾,就是放牛和学着做农活,快二十岁时,被祖父托人帮忙,送去河南潢川和麻城宋埠糕饼杂货店当学徒三年。由于战乱,日杂店被迫关闭停业,他又回家种田务农。
直到1950年末,他在本乡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至1956年任乡财粮干事。195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党员;1956年至1959年任张店公社、熊河公社辅导会计;1959年至1964年调任永河区先后任统计、会计、财政助理等职;1964年赴麻城参加“四清运动”担任工作组长,直至运动结束回永河区任民政助理、财政助理至1970年,其中由于“文化大革命”被靠边站,大部分时间在农村蹲点住队。1971年调入银行工作,先后任永河区、城关区农行营业所主任、党支部书记。于1979年光荣退休。他在工作期间多次被县区授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二
岁月不居,光阴难留,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三十三年了。随着时光流逝,许多记忆有些模糊了,只有父亲那高大的形象和崇高的品格难以磨灭,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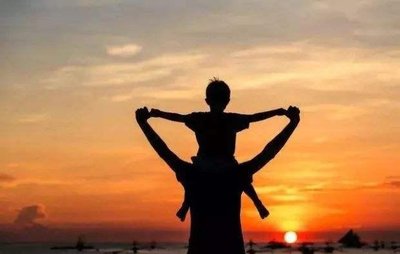
父爱
——父亲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善良人
父亲从幼年到老年,从放牛娃、学徒工、种田汉到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中,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平级同事、同志或者是下级和普通群众,对他的一致评价是:忠厚善良。除了他的慈眉善目长相善良外,更主要的是他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体现了他那来自天性的善良,贯穿着他的一生。在他退休的欢送会上,领导和同事们送给他的三句话:对上级不捧,对同级不拱,对下级不哄。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一贯与人为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有三件事最能说明父亲善良的禀性。我在小时候,就曾听乡里乡亲们传颂着父亲和弟妹分享食物的一件事:一天,父亲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从榨油房旁路过,榨房正在打花生油,榨房的师傅抓着一把炒熟的花生给他吃,他舍不得一个人吃,把花生装在衣兜里带回家分给弟妹品尝。父亲从小就懂得幸福与亲人同享、别人快乐我也快乐的道理。这故事几乎与古代的孔融让梨异曲同工,称得上是现代版的孔融让梨。父亲在职那些年,经常去农村住队蹲点,在张店公社桥垸大队任驻队工作组组长的那一年,父亲得知垸里有一特困户,粮食不够吃,经常揭不开锅,便从自己有限的粮票里挤出10斤送给那家特困户,帮助特困户渡过生存难关。其实我家也是队里有名的缺粮户,经常断粮,也要靠父亲想办法解决粮食月月不够吃的困难。父亲送了10斤粮票给那家后自己的粮票就不够当月粮票支付了,他只有找同事借粮票弥补当月缺口,下月再想办法还给人家。父亲退休后,有一次去集镇上修鞋子,鞋子修理费五毛钱,父亲见那修鞋师傅年老体弱,心生怜悯,同情他多付了五毛钱。按当时的物价,五毛钱能买7两猪肉,也可买25盒火柴。父亲就是这样,一生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急难相救,助人为乐,他做了好多善事也从不张扬,他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以上三件事是从乡亲们的口口声传中才了解到的。
——父亲是一个上慈下孝的贴心人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父母亲在管教子女的角色中一般是慈母严父,而我的家庭却不一样,我们家是慈父严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兄妹五人,人人都挨了我母亲的打骂,尤其是作为老大老二的我和大妹妹挨打挨骂在兄妹五人中是相对较多的了。可是父亲却从未动手打过我们兄妹五人。当我们惹他生气时偶尔吼两句,更多的是苦口婆心的教训告诫。全家七口人,父亲长年工作在外,拿着微薄的工资,母亲一人在生产队务农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兄妹五人,多年来一直是典型的“大缺粮户”。从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到1974年我到大队当会计这十多年间,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吃不饱饿肚子是常事。即使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父亲作为一个有担当有远见的家长,一直鼓励、支持我们兄妹五人上学读书。由于“文革”的影响,我和大妹、二妹无缘考大学,但也都高中毕业。弟弟和小妹都从全公社第一和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黄高和红一中,后来分别在湖南财大和黄冈卫校毕业。在当时农村条件艰苦、吃不饱穿不暖且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一家兄妹五人都能分别读完高中、中专、大学,实属罕见。回想起来,这既是父亲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又是父亲作为家长大人对子女最贴心的父爱啊!
作为儿子,父亲在祖父祖母面前纯良孝顺,堪称孝子。由于修建尾斗山水库,老住户需要搬迁,按当时的搬迁政策,兄弟两个的家庭必须有一家搬出原地到新地居住,因此祖父祖母和叔父一家搬迁至五里之外的“大路边”居住,父亲在一年仅有的几次回家之时总要挤时间去看望祖父祖母,嘘寒问暖并力所能及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清楚记得那是1967年11月的一天清晨,祖父突然中风,听此消息,父亲带着我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就赶到“大路边”去看望祖父,当看到祖父口齿不清,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父亲当时哭得很悲痛很伤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伤心痛哭,当时我也跟着大哭起来。父亲多方求医买药积极为祖父治疗,祖父后来竟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父亲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正直人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清正廉洁、不贪不占。大集体时,我们家是典型的大“缺粮户”,经常无米下锅,无油炒菜。父亲是我们老红专大队“四闵八湾”1000多人中唯一一位吃商品粮的“脱产干部”,又长期在本区本乡工作。当时的干部威信很高,父亲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带头实干,廉洁奉公,可谓是说话算数,一呼百应,但他从不利用职权和威信占公家的便宜,从不贪集体的好处。记得我13岁那年,因家里揭不开锅,离小队分粮还有几天,母亲叫我一大早步行12华里山路赶到永河区公所找父亲买米,我到了区公所一打听,父亲在保丰大队西张元湾蹲点住队,我又步行赶到西张元湾,在田间找到了父亲。父亲是那个时期典型的“三同”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见到我找到了田边,他自知有急事,慌忙赤着脚从田里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家里人饿着肚子等米下锅呢,父亲当即清点了身上的全部粮票和钱,只能买五斤大米,他马上向同事借了10斤粮票、两块钱,并带着我去附近的粮管所,掏出粮票和钱买了15斤大米叫我背回去,当时已是吃午饭时间,他带着我去大队厂吃“派饭”,吃完饭后把我吃的午饭按当时的规定标准,另外补交了半斤粮票一角二分钱。厂里的厂长、会计都说,小孩难得吃餐便饭,不收钱票,可是父亲严肃地说:“规矩不能破,必须收”,他硬是交了这餐饭钱。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每月都要向单位或同事借钱借粮票以解家中无米之炊,父亲那微薄的工资,每个月总是寅吃卯粮,上月预支下月的工资,他这个“月月借债人”一直过了10多年。
还有一件事是1987 年,全县信用社拟招一批新员工,我弟弟当时还在待业,我和老婆商量,请父亲来县城出面找一下领导。我老婆去买了两瓶好酒,给父亲提着,让他晚上去领导家以农行老干部申请解决子女就业的正当理由去沟通一下,父亲叹着气说一生没做这种求人的事,不愿意去,经我和老婆好说歹说做工作,他才很不情愿地提着两瓶酒出门了。到晚上九点多他红着脸回家还是把两瓶酒拿回来了。他说:“我在领导家门口来回去了三次,就是不好意思提着酒进领导的家门,只好回来了,你们看着办吧。”父亲就是这样,一身清白,一本正经,刚直不阿。后来我弟弟在全县的招工考试中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职了。
——父亲是一个吃苦耐劳的辛苦人
我家作为一个有七口人穿衣吃饭过日子的“缺粮户”,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是困难重重,最具体的是公分粮抢不进来,每个月总有五至七天缺粮吃,虽然红苕、南瓜、萝卜、白菜等也能伴米煮着充饥,但是一个月总有几天无米下锅。每逢在这个时候,我们兄妹几人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父亲的出现,父亲那时在十几里之外的永河区工作,又经常去几十里外的农村蹲点住队。他是一个特别能吃苦、能受委屈的人,经常在十几里几十里外买米背回家解燃眉之急,有时是傍晚打着手电筒照路送米回家,第二天天未亮又返回住队支农点去参加劳动。还有一次,他未跟领导请假,傍晚送米回家连夜又赶回了支农点。可见父亲是多么的能吃苦,多么的守纪律,多么的能受委屈啊!那些年,家里每年喂一头猪,由于缺粮户小队分的粮食少,猪吃的糠也经常不够,我和大妹经常去塘里打一种名叫“虾腥草”喂猪,我家的猪也由于吃不饱,比塆里别人家的猪长的慢、长的瘦小些。记得有一次,父亲在永河买了一百斤麦麸,他肩挑百斤担步行十几里山路送回家喂猪,到家时他已是汗流浃背湿透了衣衫。
——父亲是一个淡泊名利的清白人
父亲自1950年参加工作,他一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对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是领导和同事们有目共睹和公认的。但是一直到1970年,工作了20年,还是一个股级干部,在股级干部的岗位上干了10多年,组织上考虑他已年纪40多岁,想把他的职务提拔一下,由领导和组织部门干部分别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让他去干一届小公社书记(副科级),领导在征求意见时说:“8个小公社,除永河公社外,其余的由你挑选”;第二方案是平调至区直机关财贸单位去当一把手,并让父亲回家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我记得当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还是父亲很严肃认真地说:“去当公社书记,要领导和管理几千上万人,我有自知之明,做实事可以,不善变通,心善不狠,挂帅不行,万一干不好,我愧对党组织的培养,愧对群众的信任,加上身体欠佳,患有气管炎经常咳嗽,我还是去部门工作吧。”就这样父亲在1971年由区公所调入农行工作直至退休。后来听父亲的同事说,区委书记和组织部的领导评价父亲是唯一一个拒绝提拔升职的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白人,老实人。回想此事与后来不少人为提职升官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相比之下,父亲的这种平凡的本份彰显出多么的伟大啊!
父亲仙逝三十三年了,在时光的流逝中,有些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些往事却难以忘怀,以上是父亲在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段,而实际上我的父亲在他普通而又平凡的一生中,领导评价他是个忠诚踏实、顾全大局、尽职尽责的好干部,老百姓赞扬他是个克己奉公、吃苦耐劳、为民分忧解难的带头人,邻里乡亲感叹他是一个忠厚善良、和蔼可亲、助弱济贫、让人信得过的人。
三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感,它无私、深沉、如同大地般厚重,它比山高比海深,那就是父母之爱。每当我听到这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哀伤和领悟。
都说父爱如山,山在则心安,岁岁年年常思念;山高则路长,年年岁岁永难忘。我慈祥的父亲,我敬爱的老爸,您去了天堂,但我依然能感受到您的善良与坚强,慈爱与担当。您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及后代将永远怀念您!
谨以一篇祭文表达我对父亲无尽的思念!
十月二十,乃父诞辰。先父冥诞,世纪百龄。
兄妹邀约,家人同行。燃香烧纸,祭拜亡灵。
鸣呼尚飨,泣不成声。三磕九拜,以表孝心。
父生乱世,战乱纷争。幼年凄苦,家境清贫。
少年放牛,未入学门。三年私塾,务农习文。
青年学徒,外出谋生。起早摸黑,勤勤恳恳。
店铺被炸,日寇入侵。被迫回家,种田为生。
雄鸡一唱,解放战争。革命胜利,穷人翻身。
当家做主,感谢党恩。参加土改,入队前行。
财粮干事,革命阵营。从乡到区,边干边升。
财政助理,银行主任。立党为公,服务人民。
扎实做事,清白做人。尊老爱幼,平易近人。
吾父大人,可敬一生。家国情怀,赤胆忠心。
成家立业,艰难尝尽。养儿育女,茹苦含辛。
吾父一生,与人为善。坚强独立,质朴纯真。
为人儿子,牵念高堂。恪守孝道,无所不应。
为人丈夫,甘苦与共。为人邻里,助弱济贫。
退休回家,又染疾病。风湿重疾,走路难行。
高血压症,损害肺心。医治无效,父命归阴。
享年六七,儿孙痛心。阴阳两隔,难报父恩。
祈父平安,天堂无病,期待来世,再做父亲。
慈父虽去,德望犹存。子孙怀念,福泽子孙。
二零二四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滴泪而作。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闵建华,男,湖北人,大学本科文化,银行退休干部,先后在县、市从事金融管理工作,在近四十年的银行工作之余,撰写金融理论文章近百篇,其中有不少被中央、省、市级刊物选用。退休后,对研习中华传统文化、学写诗词很感兴趣,其中习作颇得朋友同事的鼓励与赞许。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