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坟坑掘到高出祖父的头一尺深了。
祖父攀着坑沿爬上来。他抖开一盘丈余长的麻绳,取绳子中段挂在脖子上,两端交叉缠住胸、腰,又绕了几匝。尔后将握着两条绳头的手膀子反到背后,跨到一个汉子跟前,默默地望他一眼,侧转身子,单腿跪地,将背后的手伸给那汉子。
那汉子慌忙跟在祖父屁股后头扑腾跪下,眼球在眶里碾出了豆大的泪珠子。他的手指忽然发了一阵子羊癫疯,磨磨蹭蹭地总算把祖父的胳膊和手腕缠起来了。
“拽紧呀——”祖父突然不耐烦地嘶叫一声,吓得那汉子绷着屁股往后一弹。
祖父这一声鬼嗥般的招呼并非充好汉找罪受,而是害怕。大凡自绑自杀的好汉,意志上并不怕死。但是当他蹦进坑里,黄土慢慢埋到胸前时,如果憋不住那股难受劲,说不定会丧失理智挣扎起来。假若绑绳太松被挣脱了手膀,他就可能蚯蚓一般从土里拱出来。那么这条光棍就算毁了,不是被人用锹锄石块砸死在坑里,就是爬出坑逃走了。
据说沿河往上游几百里,几十年前就有那么一条光棍:憋不住从坟坑里挣脱逃走,自觉没脸见人,索性去当了杀人不眨眼的土匪,犯下弥天大罪,最终被官府逮住大卸八块。
祖父这么一叫唤,把人圈子都叫瘪了。另外两个汉子急步上前,在第一个汉子左右扑腾跪下。
“记哥,你忍耐些。”说着,六只黄惨惨的手爪搭在祖父的背上,勒紧绳头,从祖父的手腕关节缠到胳膊肘,又缠到腋窝下,在祖父的手指绝对够不着的上脊梁骨处打了几个死结。
祖母使劲挤着眼珠子死死盯着五花大绑的祖父,突然不屑山羊胡子猪哼一般的鼻音,肆无忌惮地扯起年轻女人尖利的高音。父亲的号啕呈第二性征未成熟的假女中音。低音帮唱者是人圈子中的嘶哑呜咽。
在这悲怆的葬礼进行曲中,祖父一个趔趄站立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到鼻祖的山坟前,把榔头形的脑壳在坟包上狠捶了三下,啃了满嘴满鼻满眼的泥巴。再转回来向人圈子告别。他的膝下像装了滑轮,跪着急剧地旋转了一周,以三百六十度的全方位角磕拜了赵氏家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这时的天象并不阴沉悲壮。除了丝丝柔和的河风,还有悬浮在天空的太阳极其鲜艳明媚。太阳安详地懒洋洋地望着岗外的汉水。绿得极酽的汉水上一条六丈高桅的大河南扁子抖落大翼般的白篷悄没声响地泊进阳光灿烂的河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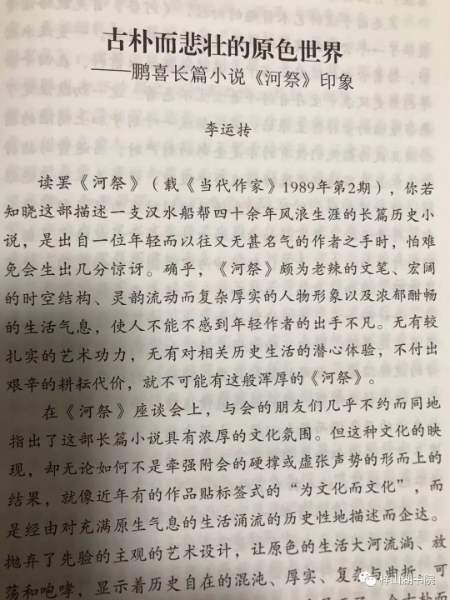
太阳宁静地慈爱地照抚着祖母。祖母像一头被打断一条腿的疯狗,歇斯底里地爬滚过去死死缠咬住祖父的双脚。她象一条被暴雨翻笞过的烂泥地里暗红色的蚯蚓在痛楚地曲扭着,鼻涕、臭汗、手肘和膝腿被地上的石子酪出的血、慌出的尿、骇失禁的粪便和粪便一样黄黄的泥巴糊满了她的全身。裤子上还豁开了一道破口子,阳光便淫邪地直勾勾地盯着破口处绽露出的一块直角三角形的雪白的屁股。总之她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女妖。
父亲也跟着爬过来.搂着祖母的脖子哭,像个小妖骑在母妖的背上。
祖父一脚踹翻母子俩人:“你要是有情有义,就守着这棵独苗把他栽大!”
说完他像飞机扔的一枚哑巴炸弹,直挺挺地插进深深的坑里。
人圈子一起矮下来统统朝消失在土坑里的祖父跪下。
“劳驾几位兄弟了,给我捧几捧老土吧。成全了大哥,来生再报大恩大德!”祖父在坑底凶狠地吼着,声音像从地狱里传来的。
依然是绑他的那几个汉子,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默默地拢去,用锹、用手、用脚,把坑沿的土坷垃掀下坑去。泪砣子也纷纷砸下坑去。索祖父命的这三个壮汉,是祖父事先郑重拜托的,他们都是自小和祖父一起厮混大的最要好的朋友。
黄土便压不见了祖父的脚丫子。压不见了腿柱子。压不见了肚皮子。
祖父像打进地里的半截粗实的木桩。黄土如魔沼陷住了祖父。
祖父像田里长的一个大红萝卜,只露出半截竖着萝卜缨子的青头。
祖母已准备好黄表、纸幡。父亲身旁的篮子里有三碗两碟供品。
人圈子橡皮筋似的缩紧了。大家惊恐或惊奇地眼睁睁地盯着双目紧闭的祖父,期待着十八层地狱下伸上来一只魔手,只要捏住了祖父的脚脖子往下轻轻一拽,他便会轻巧地从地平线上消失。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钱鹏喜,笔名鹏喜、金戈、羊角,自由撰稿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武昌理工学院教授。曾任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芳草》主编、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主要著述有长篇小说《河祭》等5部,长篇报告文学《龙马负图》等2部,散文集《梓山湖笔记》等4部,《鹏喜中短篇小说》1部。多次获得湖北省、武汉市文学奖项,多种作品入选《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和《武汉文艺精品丛书》。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