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该中篇小说发表于2017年第五期《芳草·潮》上。作品塑造了一个傻里傻气、善良纯朴、执著坚定的主人公哈古,故事发生在江汉平原,虽荒诞不经,但又在情理之中。乡土风情浓郁,人物形象突出,情节跌宕起伏。本网特予以连载,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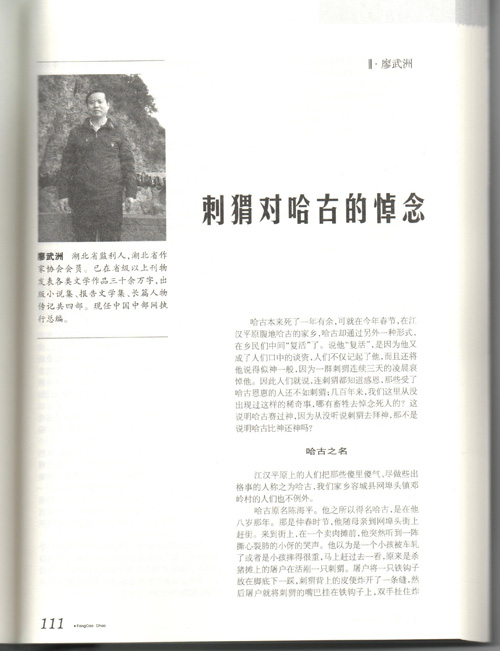
第二年的年底快到了。
在广州白云区一家三星级酒店门前,有一队保安正在出操。今天练的是正步走。但见一人总是掏腿,班长总是对那人指点不已。那人不急也不恼,总是练得认认真真。这个人就是前不久转行的哈古。
常言说隔行与隔山。当保安虽说不是当兵,但酒店的训练大纲却是按照部队的条例制定的。立正、稍息、正步走、跑步走,哈古都得从头做起。因为里头几乎清一色的退伍军人,他们对上述科目都烂熟于心,哈古每天只能开“小灶”了。
除了训练外,哈古白天要当两个小时的班,晚上要当两个小时的班。酒店当班不像部队站固定岗,可以沿酒店周边巡查。哈古除了训练间歇苦练军人基本功外,当班时他也不忘找同班的同志请教。因为苦练,加之哈古那内在的聪明劲儿,那执着的哈古劲儿,所以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哈古就基本学会了立正、稍息、跑步走、正步走等科目,经考试合格,正式被聘为该酒店的一名保安。堂客在酒店大堂做保洁,因表现积极,一个月内也聘为正式员工。
本来今年春节哈古是不想回家的,但父亲却打了电话来,说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父亲说,自己年纪大了,又经常头疼脑热,孙女明年可能带不成了,要哈古们自己带。父亲说得至为恳切,哈古与堂客经与主管部门请示,获批了过年假。
回到家,哈古见过去身体硬朗的父亲,变得步履蹒跚了,头发也成了灰白色。哈古就纳闷,记得出门划玻璃的时候,父亲可是熊劲膀劲的,仅仅两年的时间啊,人的身体怎么说垮就垮了呢?
父亲说,常言说得好,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我今年七十有七了,按七十三的说法,我多活了四年的余数,够了。
比您郎年纪大的多的是,隔壁的黄家爹今年都90了,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父亲叹了口气说,人生不害病,犹如走大运。我这病上了身,晚上肠胃老痛,头也痛,觉睡不好,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
您是有公费医疗的人,为什么不看病呢?
这两年我县上、省上大医院都去过了,吃了很多药,总是不见效,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我打电话要你回来的目的,就是担心你,你弟弟我不怎么挂心,他心眼比你活络。你这人心直,疾恶如仇,不适合做生意。俗话说,无商不奸,你又不会溜奸耍滑,这生意就不要做了。还是回来养你的鱼,种点田算了。
哈古说,我现在找了个傍坡打鼓泅的生意,我做保安,您儿媳妇做保洁,稳得很,一个月两人的工资合起来4000多。您郎见过谁傍着坡游泳淹死了的,所以说,请您郎放心。再说,现在养鱼又没什么补贴,加上好多人都在喂鱼,鱼多了卖不出好价钱了;种田现在还是倒贴,所以还得往外奔。
父亲点了点头,再不多说什么。
过完正月初八,湾上的人大都打点行装,有的准备南飞,有的准备北漂。哈古打算初九走,初八的晚上前去跟父亲辞行,父亲说知道了,又特别叮嘱说,以后就做傍坡打鼓泅的事,这样靠谱,我也安心。
第二天清早,哈古前去敲父亲的门,没有人应。推开门一看,哈古见父亲的头斜歪在床头,上前一看,原来父亲用一根带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父亲是公家人,安葬父亲,都是父亲的单位来料理的,哈古基本上没什么花费。这次响成表现得特别突出,日常接待,都是响成招呼,包括接姑妈等嫡亲亲戚,也是响成开着车去的。
父亲死了,虽然有安葬之地,可早先队里预留的两分地坟地面积,安葬哈古的父亲后,就没有位置了。为此,村民小组的组长在大家还没有外出之前,主持召开了全组的会议,讨论从哪里划一块地出来,作为新坟场。
开会之前,组长端出了一个盘子,这次划地出来,要划就划出一亩,拿田出来的农户,按当时每亩的粮食产量由组里各农户补齐。如果土地的主人不要粮食,每年就按市场价将粮食折算成钱补助到位。可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不愿意拿地,意思是按粮食折算成的钱太少了。还有的说,要折算就按亩产棉花的斤两折算成钱,因为当时棉花值钱,可大伙都不赞成这个观点。
就在会议决定不下的时候,哈古站起来说话了。他把皮带没扣实的裤子提了提说,既然大家都没个定论,我来发个言。这个地吧,也许我们死后都要安葬在此,所以我的意见是,谁的窝该谁躺,既然自己要躺,那就不能要这个钱。
哈古的意见一出,别人都说,哈古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是怕出钱吧,那以后你死了就埋在你自己的地里吧,做个孤魂野鬼。
哈古说,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我是想大家能扯出个方案的,可扯不下来。这样,我把我那鱼池旁的一亩地拿出来,做新坟地。我呢,一分钱也不要大家出。
哈古,现在不是毛主席时代,没有那样大公无私的人了。什么?你不要一分钱,你在哄小孩子吧?
哈古说,我说的是真话。反正我那是低洼地,一下大雨就渍水,每年靠天收。这块地不如拿出来做坟地好。
有人说,那地好是好,就是太低。
哈古说,低了可以把那里填起来。至于填的土,就用我渔池上的,反正现在喂鱼也赚不到钱。
有人说替哈古考虑,如果这样的话,你不是废了几亩地了?
哈古说,那地是原来队里给了我好处的,一亩地只算5分。我呢也不亏,即使把那渔池的地加上,我也不亏。
组长见哈古说的是真话,马上拍板说,虽然哈古不要钱,但我们从良心上讲过不去。我看这样,我们还是折成粮食给钱,大家说怎样。
大伙一合计,全组30户,按每亩地当年产粮食计算,一季中稻只能产1000斤左右,市场价每斤0.6元,那也只600元,每户一年只拿20元钱左右,所以大家一致通过。
晚上回来,堂客责问他为什么又哈里哈气的表态,是你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还是你要这600元打棺材钉子?
哈古说,这你就不晓得我打的什么算盘了。我告诉你,我不是无缘无故表这个态的,我是为我的那些剌猬们着想,今后那儿成了大坟场,有了那么多鬼,谁想祸害剌猬们都难。你说我值不值呀?何况我每年还能得到600多元钱呢!
安葬完父亲后,哈古与堂客启程前往广东。临走,响成突然来送行,又塞给哈古500元钱。哈古坚持不收,说上次你给我送了路费,这次无论如何不能要。响成说,我运气比你好点,每年生意上还过得去,你们两口子拉家带口,在外面讨生活不容易。我是经历过打工奔波的苦的。帮衬你们一点,也是我这个哥哥应该做的。
响成的话说得多得体,哈古就不再推辞。只好说,响成哥,那就不好意思了,等我们日子过好了,这人情我们会还的。
在广东打工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了两年,哈古一家经济上也略有起色,除去开销、两个孩子读书,还落成了3万多元钱。那晚,哈古和堂客盘存,望着银行卡,两个人盘算盘算,如果再打3年工,那手头也有十来万了,回去足可以把自己那破瓦房换成一个两层楼的小洋房。再干个六七年,哈古从心里计算,就能拿出一笔钱,然后租几亩地,进一步扩大剌猬活动基地,那时,剌猬们的活动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大,生命保障就会更加安全一些。
然而,人算总是不如天算。
那晚,哈古当班,一桩突然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凌晨两点,保安部来了个紧急集合,包括值勤当班的哈古在内。酒店的安全主管宣布一项重大决定,要全体保安迅速查找十分钟前从18楼上扔下的一张纸条,连同一起扔下的一个银质发钗。宣布完毕,主管让保安队副队长带队搜寻。队长留下来另外有事,并点名将哈古和另一当班的保安留了下来。
酒店保安问哈古,你是不是确实没有看到楼上扔下来的东西?
哈古说,之前我已经向天发过誓,谁检到谁今后被雷劈死。您还要我发什么誓?
主管又问另一个保安,那保安说,我还是原来那句老话,当时我在北边巡查,扔纸条的窗户在南边。无论怎么扔也不会扔到北边来吧?
那好,我们不是不相信你们。但今天这事非同小可,我们务必要搜查一遍。你们不要有想法?
哈古说,这个黑锅我不背,要搜你们快点搜。说着,把上衣脱了下来,将上面两个口袋拉了个底朝天。随后又将裤子的两个口袋如法炮制。然后问,还要不要把裤衩脱下来翻翻?
主管和保安队长相互用眼睛示意了一下,觉得再查下去也无意义,就挥了挥手,让哈古出去,接着查下一个。
下一个保安与扔纸条的事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们只简单询问了下,就让他离开了。
全体保安查找纸条的事情还没完,警车呼啸而至。警察一进门,就封锁了酒店的所有通道。经搜查18楼,共查获嫖客12人,解救少女8人。
那包裹银钗的纸条到底飞到哪儿去了?竟一时成了无头案。
其实这个无头案与哈古大有关系。
当时,当班的哈古正巡逻至那儿,忽然“啪”的一声从高空飞坠一白色物体,哈古迅速上前检起一看,只见上写“救,18”。他知道这个酒店开始犯罪了。哈古之所以判断这个酒店已经开始犯罪,因为前两天酒店用一辆面包车载来了7、8个少女。酒店为了看管他们,曾在保安队员中挑选了4名身强力壮的保安,本来队长推荐了哈古,但主管认为哈古虽然工作负责,可是年纪超过了40岁,长像也不精神,就把哈古的名单划掉了。
怎么样把这信送出去呢?哈古想,自己当然不能跑去报警,因为楼上很快就会有人下来查找,这时楼上刚上去一批客人,那里灯火通明,丢银钗的人肯定逃不过管理者的眼睛。情急之下,他忽然想到了出租车,这里离门前的湖滨大道仅十米之遥,如果他能在几秒之内跑过去,将信丢到出租车内,那么这位丢银钗的少女就有可能被解救;万一不能成功,自己被他们搜出,不仅免不了挨打,相反还会因此丢饭碗,这位丢银钗的少女就会遭受蹂躏,那这样就毁了一个少女的一生啊!于是,他几乎用足了十足的力气,箭一般地冲上了滨湖大道,这时正好有一辆出租车通过,虽然上面亮的有载客的红灯,为了逼停这辆车,他站在了车的中央,一下子就把那辆出租车逼停了。他马上将那包着银钗的纸条连同银钗一起塞在了司机的手里,又箭步跑回了自己岗位。
他刚刚喘息过来,上面的保安就下来了,向他盘问了一阵。之后就出现了保安全休集合的闹剧。
天明之后,酒店决定除留下保安队队长外,其他保安队成员一律遣散。就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同时,酒店遭到警察查封,负责人因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被逮捕,酒店因此停业整顿。这就是说,哈古即使不被遣散,也逃脱不了下岗的命运。
事后,堂客问哈古,你捅散了一个酒店而丢了饭碗后不后悔?哈古说,我的老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是在做善事呀,有啥后悔的。再说,现在到处需要人,我把高工资不要,哪儿找不到打工的地方!
七、梦想漂到天边的哈古
事实正如哈古所说的那样,哈古失业没到一个星期,他和堂客又被聘为一个街道办事处的环卫工。这里虽然包吃包住,工资也和酒店差不多,就是两人不能住在一块,而是男、女分开住。哈古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毕竟结婚十多年了,同不同房不重要,天天能见着就行。
环卫工虽然要起早贪黑,但每天的工作量不大。哈古和堂客各人负责一条近300米长、8米宽的街道,凌晨5点起床后清扫一遍,之后每两小时巡查一遍,发现有垃圾和纸屑就扫进撮箕里,标准是只要路面看不到垃圾和纸屑就行。哈古很看好这份工作,他谈起来说,尽管这份工作看起来很低贱,可每天扫垃圾还能捞点外快,就是从垃圾桶里每天能捡近百个饮料瓶和上十斤废纸,也能卖个十来块钱,仅凭这个,两口子每个月的外收入也有600来元,这样的生活大约持续了8年之久。
第9年的头上,那年广州的气温相比往年偏低。一日,哈古突然感到膝关节不适,之后就钻心地疼痛,疼得他几乎站也站不稳了。这阵剧痛大约持续了1个多小时,之后才逐渐减轻。事后,哈古也没把这事当个事,依旧做好他的本职工作。
时间倏忽之间过去了3个多月,就在哈古逐渐淡忘膝关节疼痛之间的事之后,那天凌晨哈古刚刚把自己承包的那条街扫完,突然感到膝盖处疼得比以往更加钻心,随后就站不起来了。他没有急着给堂客打电话,他抱着还等等还等等的想法,说不定这时就不疼了,就能站起来了,直至中午,他觉得站起来无望,这才给堂客打电话。
之后,就是向单位请假,先后在广州好几个大医院就诊过,最后确诊为风湿性关节炎。哈古知道,自己该得这个病,因为在家种田时,每逢春秋两季插秧,自己都泡在水里;来南方打工后,住的是地下室,潮湿重,湿气侵染那是躲不过的。
确诊后,吃过一些医院开的药,根本无济于事。哈古只好求助于游医郎中,可是经过几个回合的治疗,花了大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效果。几经病急乱投医,哈古终于找到一个打封闭针的医生,此种办法就是将药剂从膝盖处注射进去,这一针进去,能管个三五天,然后疼起来了又打,每一针需要150元,这样断断续续诊治了一年,加上起初诊病花的钱,共花了近两万元,等于说一年上头白干了。
年底,哈古本来想回一趟家的,可堂客说,这一去一来,车费及有关费用又要花两千多,我看还是不回去的好。哈古知道自己家里经济已经亮起了红灯,因为去年女儿出嫁带了5万元彩礼,这是必需的,也是哈古咬紧牙关拿出来的钱。所以手头的积蓄也用尽了,因此他放弃了跟堂客做工作,又窝在广东过了一个年。
年头,哈古虽然觉得病情有些严重,虽想放弃上班,可放弃了上班,打封闭针的钱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因此,初一到十五他为别人顶替了3个班,这样能多挣300元钱。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哈古想起了响成的舅爷,响成的舅爷那可是一只腿跛了,一只眼瞎了,他又是怎样在过呢?他难道不需要钱诊治吗?
想起响成的舅爷,他心里开始愧疚起来。于是,他开始酝酿一个计划,他要用两到三年时间,筹集1万元钱,寄给响成的舅爷,作为自己对他的补偿。2014年年底,当这笔钱筹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觉得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没有办,今年务必要回家一趟,这件事对他来可说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堂客就家庭经济窘况,本来是不想回家的,想想快有十来年没有回家了,也支持哈古的决定。
这年大年三十他要求儿子和他一同守岁。儿子林林今年二十有二了,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念的是电子专业,翻过年来7月就要毕业,现在在一家企业实习。这是哈古最感欣慰的一件事。儿子见父亲第一次这样做,就问今年可是鸡子屙尿,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您郎为什么要我这样做?
哈古说,今儿个我们父子俩好好聊聊。这也是传统,祖祖辈辈们传下来的。有些事我要传给你。
往后的日子多着呢,干吗要今年传?
黄泉路上无老少,万一我哪天走了,一些传统没有往下传,我到了那边阎王爷也不会饶我。
于是父子俩就坐下来开始聊天,哈古说家里有几亩地,还有一口渔池。这口渔池一直承包给别人,过去因为养鱼的人多了,承包金一直比较低。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我们就把承包金调高了些,一直到现在没调。今年我们随行就市,与承包人协商,将承包金由2000元调到3500元。哈古又和儿子聊了聊学习上的事,问儿子什么时候毕业,今后打算在哪里工作等等。不知不觉,守岁的钟声敲响了。
哈古马上倒了洗脸水,洗净了手,又沐浴了脸,之后在神堂前向祖宗牌子作了三个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虔诚地点燃一摞香,将神柜上的三个香碗每个碗插了3支,又到灶门口、屋前屋后等地都插了3支,随后就让儿子去放爆竹。
这时,爆竹声此起彼伏地开始响起。哈古出得门来,向四处远眺,夜空到处烟花璀灿,远远近近的村庄灯火通明。十来年没见家乡这种美丽的夜景了,今天见到,哈古自然有一种亲切和无比幸福的感觉。然而,膝关节处又开始钻心地疼痛起来,身子好像又站不稳了,他没等到儿子放完爆竹,就回到了屋里,吃了几颗早已预备好的止疼片。
儿子放完爆竹回到屋里,问父亲还有什么事,哈古说,当然还有,等一会我们一起去办件事。不长时间,止疼片发生了作用,哈古让儿子提起桌旁的一个装着稻谷和玉米的袋子,说我们去天官庙。
儿子诧异,说黑灯瞎火的,提这些个东西,干什么?
我们过年,动物也要过年。
儿子早就听说过父亲保护剌猬的故事,可没听说父亲给剌猬过年。难道自己手里提的是剌猬过年的食物?父亲回答说,稻谷和玉米是剌猬较喜欢吃的粮食,它还喜欢吃红薯叶等食物。
他们来到天官庙那片乱坟岗时,哈古让儿子将稻谷和玉米撒了出去,方圆有三十来个平方米。于是,哈古拍了几下手,就和儿子来到一旁,静候剌猬们的到来。兴许是哈古和剌猬早有默契,一会那些剌猬都爬了出来,纷纷向有食物的那块地方靠拢。
虽然年三十的夜晚黑咕隆冬,由于哈古和儿子来时就摸黑前进,眼睛早已适应了这漆黑的夜晚,眼前的一切依然看得明明白白。儿子一看眼前的情景,差点喊出声来,哦,我的妈呀,好多剌猬,少说也有七八十只。当儿子看清了眼前的一切后,哈古拍了拍儿子的背,小声说,我们走,不要惊了他们,剌猬是个喜静的动物。儿子以前听说过父亲买剌猬放生的故事,可不知道父亲还与剌猬有这些默契,他此刻觉得父亲爱剌猬没错,虽然为此还得了个哈古的浑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父亲的这个爱的权力应该得到尊重。
病上身了,要甩是甩不脱的,如果要甩脱,那只有彻底解脱。从家里回广州后,哈古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一定要在珠江涨大水时实施。
哈古虽然拟定了这个计划,到时实不实行,他也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当年5月又发生了一件让他十分闹心的事。
这年5月,女儿离婚了。女儿虽然有工作,但女儿有志气,她决不继续在丈夫的公司里苟活,愤而辞职。女儿本想住几天后就出去另谋新职,可是由于心情不舒畅,就一直在家住着。不久,儿子也毕业了,虽说学的是软件专业,工作好找,可录取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也窝在了家里。
这样,家里的生活就开始吃紧了。哈古的工资以及每月捡废品零星的收入,只够他打封闭针和看病的,有时还不够,哈古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因为他感到养活自己都力不从心,何谈养活两个伢儿?因此,他觉得这样活着再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天清早,他跟堂客说,你今天帮我把最喜欢穿的那件白色褂子找出来,还有那件透气的亚麻裤子。堂客问,你要走亲戚呀?哈古说,今天这事比走亲戚重要,我负责的那条路要搞检查,有领导要来,主管班长说要我们都穿得精神点,跟他长点脸面。
堂客说,原来也搞过检查,你为什么没有要穿好衣服?哈古说,主管班长强调了,我们总得跟他长个脸面吧。堂客说也是,马上替哈古把那两件平时哈古最喜欢穿的衣服找了出来。
哈古又喊儿子跟他洗个头,儿子林林说,爸爸从来没叫我洗过头,今天是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哈古说,今天领导要来检查,所以我要享受儿子提供的服务。儿子洗完说,今后只要爸爸有出彩的事,都由我来洗,我保管您郎每次都精精神神。哈古说,只这一次就行了,哪老有领导来检查的呢。
哈古洗完头,来到镜子前照了一遍,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提着撮箕,拿了扫帚径直出了门。
不一会,林林接到了哈古打来的电话。哈古说,你跟你妈说一声,我再也不会吵你们了,今后你要孝敬你妈,爱护你姐。我林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哈古说完,就关机了。
哈古到哪里去了呢?
他来到了珠江大桥。这座桥在1963年评选新羊城八景的活动中,由于珠江大桥象天上垂下的两条彩虹,跨在银光闪闪的两条珠江支流上,四周的田野一片翠绿。而入选新羊城八景之一“双桥烟雨”。这里的景色虽然很美,但哈古却没有半点心情欣赏。他这时候思索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再不给家人添麻烦。他来到珠江大桥中央,见这里水流最为湍急,甚至水面上不时出现大的漩窝,他想如果从这里跳下去,要不就会被漩窝卷到水底去,最好被沙子埋住;要不就会随着湍急的水流漂到海里,让家人找不到,这样就不会给家人添麻烦,不会让家人为自己花一分钱。他觉得这个计划最为完美,想定之后,他就用手机给儿子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然后就翻过护栏,纵身跳了下去。
然而,哈古的梦想终于没有遂愿。他虽然被湍急的江流吞没了,可既没有被卷到江底让流沙盖住,更没有被漂到海里去,江水而是将他的尸体冲到了一个回湾里。这个回湾离珠江大桥不过四十来里地。
儿子林林自接到哈古打来的电话后,对父亲的没头没脑的话,感到一头雾水。于是专门跑到妈妈上班的路段,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你爸爸是一根筋,可能是哈气又上来了。
可是到了晚上,哈古并没有回家,打电话又关机。这下家人开始着急了。全家人先是到哈古所在的路段问了当班人,当班人说,哈古今天并没有来上班;那您这儿今天又没有领导来检查呢?当班人说,领导的毛都没看到,哪里有人来检查。堂客这才慌了神,就给自己的姨父打电话,问哈古到没到他们那儿去,那边说没有;另外哈古在这边没有朋友,他也确实无地方可去。是不是回家了呢?于是他们又跟哈古的兄弟打了个电话,如果哈古回去了,请打个平安电话过来。家人又分析,是不是出事了呢?林林跟他妈建议,既然爸爸在这边无地方可去,那是不是出了人命案还是其它事呢?于是,全家人去派出所报了案。接警警察先作了登记,并告诉他们说,你们全家还是先找找,如果没有消息,三天后你们再过来一下。
第三天上午,林林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认尸启示,说有渔民在一个回湾处发现了一具尸体,身高多少,并播放了画面,请失踪者的家人到某某殡仪馆认尸。
林林跑到殡仪馆一看,除了身高像父亲外,其它地方都面目全非,身上到处被鱼咬了一个又一个的洞。于是,林林打电话让妈妈赶了过来,林林的妈妈一到,见到哈古穿的衣服,马上就哭起来了,哭着说我的姊妹,你骗我说领导要来检查,要穿你喜欢的衣服,原来你是做哈事去了……
林林马上给在银行工作的叔叔打电话,说已经找到父亲了,现在正在某某殡仪馆里。公安方面说,现在还不能领尸,还需做DNA鉴定。
叔子接到电话后,当天搭承武汉到广州的航班,很快赶到了目的地。经DNA检测,证明是哈古无疑。
哈古之死,不仅没有遂他死的愿,也没遂他不找家人麻烦的愿。相反给家人添了更大的麻烦。从DNA鉴定,到付殡仪馆火化费、还有家人来往的路费以及安葬费等,远远超出了万元以上,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花得所剩无几。
因为事发5月,5月是一年里赚钱的黄金月。族里除了几个老人外,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虽然发去了信息,大家都忙着赚钱,没有一个人回来参加哈古的葬礼。连哈古的亲堂哥响成因为包二奶东窗事发,正在跟老婆闹离婚,也没有回来,只打来电话对哈古之死表示了哀悼,并责怪哈古不会享受生活,年轻轻的想不开。所以哈古的葬礼,除了娘家来了几个人外,陈姓参加葬礼的包括老幼在内也只有七八个人。送终时,哈古的堂客见门前冷冷清清,就哭着说,你真哈,连死都不会死,要死就选个冬天什么日子的,那时候送你的人多。你枉为人一场啊,姊妹!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